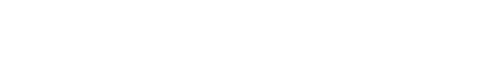思想者第559期
思想者第559期要鼓励艺术机构考虑如何减少其他方面的开支,而保证艺术创造,考虑如何将大部分的钱集中到制作一场好的演出,然后找到一个积极的方法去营销这些精彩的演出,这样才可以拥有观众,然后有了吸引赞助商的基础
把精力投向、资金投向、人才投向聚集在哪里,怎样在文化软件建设上下对工夫,这个难度恐怕远远胜过对硬件投资的百倍千倍
思想者小传
陈圣来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 《大型特色活动与特色文化城市研究》首席专家。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特约研究员,美国加州大学奇科分校荣誉教授、纽约理工大学特聘国际咨询专家、韩国国乐教育国际顾问。历任东方广播电台台长、总编辑。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总裁。2010年当选为亚洲艺术节联盟主席,两次被世界节庆协会授予“杰出中国人物奖”。2011年担任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出版有《生命的诱惑》、《广播沉思录》、《晨曲短论》、《品味艺术》、《艺术节与城市文化》 等多部专著。
对上海这座正在建设为金融中心的城市来讲,要提升文化软实力,当然一定要有资本的介入,包括国际金融资本的介入,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一旦资本介入了以后,也会碰到很多的矛盾和困惑。这里确实有二律背反的问题,我今天主要讲两对矛盾,一对矛盾是创意和市场的矛盾; 第二对矛盾是软实力中软件和硬件的矛盾。这两对矛盾其实都是软和硬的矛盾,第一对矛盾讲创意和市场,实则也是软和硬的矛盾,往往创意比较软,而市场比较硬,因为市场牵涉到真金白银,于是创意屈服于市场,当然,市场本身也有个软硬问题。所以总体来讲,都是软实力的软和硬的问题。
软与硬:艺术创意与资本逻辑
第一对矛盾,创意和市场的矛盾。前年我率队参加了台北举行的四城市文化会议,台北、香港、深圳、上海这四个城市的文化学者会议已经连续举办十几年了,每年每个城市出个议题,轮流做东,是个很专业很有质量的会议。前年会议的总议题是“文化政策与城市发展”,其中一个分议题就是“在资本主义逻辑下的文创危机”。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个命题?我认为,在资本的介入和结合下,文创应该会显得特别生机勃发。因为,文创要落地,要转化,要结果,都离不开资本的扶持,这样的例子在全世界都司空见惯了,不胜枚举。所以在资本的逻辑下,文创不应该是危机,更可能是转机和契机。资本和文创构不成矛盾关系和对立关系,应该是携手促进的关系,和衷共济的关系,我们文创工作者要善于凭借资本去撬动文创的发展。因此,资本与文创危机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和因果关系。
到了台北参加讨论以后,我才明白港台文化工作者提出这个议题的道理所在。香港有一位年轻的影视工作者卓祥,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讲到拍一部实验性影片的经历,很感性地诉说了资本对于创意过程无处不在的干预。台湾也有学者陆离真批评台湾在文化产业化和产业文创化的思路下单纯强调经济效应,结果使文化公民权难以获得切实的保证,同时使一些真正具备原创价值的元素因为无法产业化而难以得到扶持。资本是逐利的,和文化并不一定是相向而行,所以当资本和文化嫁接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矛盾,产生撕裂。故而在台湾和香港会提出这样的命题,是因为在资本的逻辑下确实有文创的危机,资本的逼仄使文创缺乏自由生长的空间。
他们认为,如果一味计算投资的绩效,对从源头上扶植创意人才是无意义的。所以,资本逻辑下的文创危机是文化的病态,其症结在于,业界和政府、文化机构不自觉地把产业系统的生产模式变成了文创政策的思维模式,以产业的视角主导了文化创意,着眼于经济活动的过程,而忽略了更广阔的社会、文脉和价值。
经过讨论,这些港台的文创工作者提出来的问题,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他们的困惑也值得我们思考。这个思考和反省可能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我觉得从政府层面,以及以政府为主导的包括公益机构的层面上,在整个文创的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首先政府不能缺位,港台的症结是政府缺位,或者讲,政府不作为。我认为,政府要积极地出面,并推动社会公益机构一起,无功利目的地去支持一时投资绩效还不能显现的文创项目与人才,不要过早地让市场压迫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而另一方面,政府不能抢位。我们与港台社会机制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社会这一层比较成熟,因此许多事不一定需要政府出面; 而我们政府比较强势,社会这一层却很弱很稚嫩,因此政府干预得也比较多,结果往往是政府的意志替代了市场的意志,从而左右了文创人员的意志。
其实,在文创方面台湾有很成功的案例。比如,台湾的艺术门类很齐全,也有许多政府出资的文艺团体,但真正能叫得响、代表台湾的大概非“云梦舞集”莫属,而这是台湾的一个私营舞蹈机构。记得我20年前到法国、到德国,当时所到之处所遇之人都和我讲中国文化,为什么?因为当时正好是陈凯歌的 《霸王别姬》 走红,在欧洲几乎逢人都和我讲,一部电影就大大提升了我们的影响力。但是之后将近20年,我的足迹依然在世界踏勘,却几乎没有一部中国电影引起外界人士与我交谈的。相反,他们有人在不断地和我提起这个云梦舞集,这在世界上是公认的优秀的现代舞团。我们上海国际艺术节也隔三岔五引进云梦舞集的剧目, 《竹梦》、 《行草》、 《红楼梦》 等,都是非常有创意的,不光是一个舞蹈演出,而是非常有创造价值的舞台创意。与云梦舞集相比,我们没有一个这样响亮的民营团体。这个需要引起我们的思考。
当然,这里也有文创界本身的责任。传统意义的文创已经受到严峻的挑战,面临很大的危机。面对新的形势,我们一定要懂得利用资本的元素去撬开市场。面对市场,文创要善于凭借资本的力量,来壮大自己。如果你个体不行,就要组成团队,要弥补这一市场的欠缺。
弱与强:谁能决定卖多少票
我曾经邀请美国国家艺术中心的总裁凯撒到上海艺术节来做过一个讲座。此人在业界鼎鼎大名,在文创界是被誉为有“起死回生”之术的大师级人物,他跟我说,艺术是困难的,并将越来越困难。为什么?
首先,这个领域不同于其他的产业,不可能提高生产力。钢铁也好、汽车制造业也好、IT行业也好,都有机会提高产品生产力。但是在表演,特别在表演艺术领域(在视觉艺术领域同样如此),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两百年以前莫扎特创作的歌剧《唐璜》,我们至今还维持着他当时写这部歌剧时候的演员的数量。我们演过好多当时的古典歌剧,都是当时的剧本,当时的音乐,当时演出的人数,你不能去改动,不能减少人力物力,也就不能减少财力。我们不可能像其他的产业一样通过改变材料,或者改进技术手段来降低成本,来提高生产力。这就是为什么艺术越来越难、越来越贵。
第二个问题是观众人数限制导致了它收入的限制。比如有一个剧在200人剧场里面演出,就是固定了200个人的收益。在上海大剧院演出1670个位子,就是1670个位子,大不了在走廊里面加一些位子,变成1690,这是物理空间规定的。唯一我们能够改变的是性价比,我们提高收入的方式就是提高票价,到现在我们的票价已经提高到老百姓难以忍受的程度,票价贵已经成为一个公共性的问题,当然也是世界性的问题。
票价越来越贵,于是大家采取错误的方式进行应对。往往大家会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在艺术创作方面,创作更少的作品,为了节省成本,不断地重复演出以前的作品,选择做小规模的作品,而更少制作大规模的作品,以减少投资。第二件事情就是减少市场营销的支出,大幅度削减广告营销开支。这样就进入了一个困境和怪圈:艺术作品的减少、市场的减少,收入也相应减少,于是更少的资金、更少的投入、更少的收入,这样循环往复,直至艺术机构病入膏肓。凯撒当时讲的一段话非常精彩,我记下来了,他说,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能生存下去最重要的经济原因是令人兴奋的艺术。所以要鼓励艺术机构考虑如何减少其他方面的开支,而保证艺术创造,考虑如何将大部分的钱集中到制作一场好的演出,然后找到一个积极的方法去营销这些精彩的演出,这样才可以拥有观众,然后有了吸引赞助商的基础,确保有足够的费用花在艺术创作和市场营销上面。这种观念改过来,就会进入到一个越来越良性的环境中。
凯撒曾挽救了美国一个黑人舞蹈团—“阿尔文·艾利”舞蹈团,将它从一个无人知晓的舞蹈团培育成了世界上顶尖的舞蹈团,在纽约还有一条街道是以“阿尔文·艾利”命名的。我们曾请这一舞蹈团来艺术节演出《火鸟》,确实很令人震撼。美国的芭蕾舞蹈剧场、英国的皇家歌剧院,都一度濒临破产,然而是凯撒使之起死回生。他说:当时能够挽救过来的原因,就是我尽可能在其他方面节省钱,但一定会把大把的钱用在市场营销和艺术创造上。事实上我能够成功经营艺术机构的关键,便是好的艺术作品加上好的市场营销。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艺术机构有非常好的艺术创作和一个强有力的市场营销,却是没有收入去维持的。
凯撒以他的经验之谈,对弱和强做了一个形象的解说。他说:做艺术要做得非常特别,因为当你的艺术非常特别时,你的购买者就变弱了,这是非常主要的一部分; 另一部分是做一个非常好的市场,如果你的市场做得非常棒,如果人们在报纸上、在电台里、在电视上都在谈论你做了什么,讨论你有多特别、多棒,就能使购买者想来看你,使他们的市场地位变弱。如果你做了很好的艺术,然后你的市场营销做得非常吸引人,你就可以削弱购买者的地位,你就能卖出更多的票子,得到更多的收益。他这里说的弱和强,就是我们讨论的软和硬。
所以,综上所述,无论是政府、资本还是市场,他们和文创,都可能是对矛盾,都可能存在“软”与“硬”的问题,但是关键是文创不能软,文创一软,势必就陷入凯撒所讲的恶性循环的“困境和怪圈”里。当然市场也不能软,这里的市场讲的就是市场营销,实际上,我们这一块非常弱。我们平时一讲市场往往讲的是客观市场(文艺产品的静态消费市场),而没有关注主观市场(由文艺产品经营者通过营销行为主动创造的消费市场),因此就缺乏对市场的驾驭能力。
创新与保守:要敢于冒险探险
按照约瑟夫·奈对文化软实力的定义,讲到底就是文化吸引力,这个我自己觉得有很深的体会。在90年代初期,上海的文化软实力是非常弱的,这首先体现在硬件上。上海最早引进世界十大交响乐团,第一个引进费城交响乐团,是我参与引进的。当时把费城交响乐团引进来的时候,没想到偌大个上海竟没有一个剧场可以供其演出。当时上海最大的剧场是市政府大礼堂,但其时市政府大礼堂已经损坏并废弃不用了,于是堂堂大上海竟再也找不到一个剧场的舞台能够容纳下一个完整的交响乐团。最后我们万不得已选择在万体馆,在体育馆里面搭了个音罩,放下一个交响乐团,而观众坐在欣赏体育比赛的简易座椅上聆听交响乐团演出。你想上海之大却没有一个能够容纳世界名团的立锥之地,这就是当时令人啼笑皆非的状况。以后,我又看过一场世界名团的演出,祖宾·梅塔指挥的以色列爱乐乐团音乐会,当时是在上海展览中心召开“两会”的会场演出的。如此的上海怎能迎候世界一流文艺团体,怎能跻身世界一流城市的行列?这样的城市遑论什么文化软实力。所以提升上海文化软实力首先必须从硬件开始,自90年代中后期以后,上海开始痛定思痛,从大剧院到东方艺术中心,到上海音乐厅、图书馆、博物馆,一直到现在有了文化广场,有了世博演艺中心,还有了上交音乐厅,不久,还会有虹桥的国际舞蹈中心、上海历史博物馆、新的刘海粟博物馆,等等。上海整个文化硬件设施这几年有了长足的进步,就我所到过的世界上各大城市,可以负责任地讲,上海现在的文化设施,特别是演艺方面的硬件,是不输给世界任何一个城市的。现在国外如欧洲很多艺术团体,都说将来要把演出中心转到我们亚洲来,像上海、新加坡、日本这么好的剧场,他们都没有。
现在上海是硬件很硬,但另一方面,相比较文化硬件,我们的软件很软很弱。尤其一旦文化硬件快速崛起和坚挺,更映衬和凸显了我们文化软件的疲软。近几年实际上我们下了很多功夫,但收效不大。比如说上海现在的民办社团很羸弱,全上海文艺社团594家,但是民办社团只占2.7%。中国第一家上市的电影民营公司华谊兄弟、中国第一家上市的旅游演艺公司宋城、中国第一家上市的电视剧制作公司华策都在浙江,而不在上海。还有一些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活跃的民营演艺机构,包括电影机构,现在都在北京,电影的后期制作70%是在北京完成的。文学艺术界的一些实力人物,一些耳熟能详的品牌都不在上海。
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我们现在讲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观念创新都不够。对文化,我们过去基本习惯于管控思维,这种管控思维到现在还存在,站在这样的基点上,对文化就不是想办法去释放、鼓励、疏导,而是去防范、管压、控制。
过去一直讲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这是对旧社会上海的特指,是含贬义的。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忽视了“冒险精神”对文化的积极含义,正因为一次次的冒险,上海在全国率先有了远东最大的电影院大光明电影院,有了最大的游乐场大世界游乐场,有了最大的舞厅百乐门舞厅,有了最早的交响乐团,有了最早的电影制片厂,有了最早的流行音乐以及一批享誉全国的作家画家艺术家,包括出版家编辑家经纪人。艺术是需要冒险并鼓励冒险的,英国爱丁堡艺术节总监麦克马斯特爵士说,如果艺术节不去冒险,那就只会走下坡路。伦敦国际戏剧节创始人罗丝·方登说,艺术节是允许你冒险的地方。艺术节如此,艺术何尝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冒险精神”。冒险就是探索,就是创新,就是突破常规,挣脱窠臼,毕加索不冒险?马蒂斯不冒险?勋伯格不冒险?马尔克斯不冒险?当时他们的出现都引起轩然大波,然而他们在引起争议之后,一个个都成为公认的大家,成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难以逾越的高峰。艺术忌讳平庸拒绝平庸,而陷入平庸最大的危险就是不敢冒险。上海如果能够重新在文化的创造、文化的营销上,鼓励并形成一种冒险精神,或者讲探险精神,我们的文化肯定会有一个不同的面貌。
上海应该要考虑,在提升文化软实力方面,在软和硬的制衡上怎么下工夫?我们要把精力投向、资金投向、人才投向聚集在哪里,怎样在文化软件建设上下对工夫,这个难度恐怕远远胜过对硬件投资的百倍千倍。
(陈圣来系亚美平台官方(中国)有限公司杰出校友)